附录 12月2日周二 课后关于参量域的讨论
郑子拓:今天公司组织AI分享,一个细节引发了很多思考,结合汪老师教授的内容,丢出一些感想。
从人工智能到管理与成长,为什么都逃不过这条规律?
上午公司有一场 AI 发展的分享,一个细节引发了很多思考。Hinton 早在 1986 年就证明了:反向传播(Backpropagation)可以有效地训练今天我们大范围使用的神经网络——这一点在丁丁老师的课堂上也讲到过。然而,这个现在看是开天辟地的成果,在当年几乎没人理,在 26 年以后才因 AlexNet 横扫 ImageNet 而爆发。而 1990–2010 整整 20 年,统治人工智能领域的是一套叫做统计机器学习的方法。
为什么一个理论正确的东西,要等几十年后才有价值?
这让我想到很多,不仅仅是 AI,管理如是、人生亦如是。
很多正确的东西,需要规模才能发挥价值。Hinton 的理论没有错,但在那个时代:数据不足、算力稀缺、工具链尚未成熟、复杂度还没到需要“深度结构”的程度。深度学习不是没价值,而是样本规模太小的阶段容不下它的价值。
管理如是!
为什么创业公司讨厌流程,而大公司没有体系化管理会直接崩盘?创业初期的小组织靠灵活取胜,成熟的大组织靠体系稳定。五个人靠默契、五十个人靠沟通、五百个人靠流程、五千个人靠制度。体系不是没有价值,而是组织规模太小的阶段容不下它的价值。
人生如是!
为什么我招的一些毕业生在学生时代成绩卓越,入职后难得高就?上学时任务单一、评价单一、变量可控,而现代工作中少有独立一人无需协同即可完成的任务;关系网复杂、信息高度不对称。我常跟团队们说,逻辑和人际这两项通识能力,是工作的底层能力,遗憾的是学校并不教授,需要有意识地自主学习。通识能力不是没价值,只是在参数规模太小的人生阶段容不下它的价值。
(停在这里思考了很多,显然作为为人父母,这涉及教育下一代的问题,权重大过其他问题。)
至此不由得想起读 Geoffrey West 的《规模》时的一个朴素感受:“大了就是不一样!”从动物代谢、到城市创新、到个体认知、到企业组织,我想有理由推演到更宏大的范围:一切真正能承载大规模系统的东西,都有共同特征:慢、深、重、看似无用,但可长期积累、高度复用、能在复杂度面前保持稳定性。
就像开篇引发我思考的 Hinton 的那个问题,原理正确并不难理解,制约其价值的首先是规模,再进一步,是惯性。
在小规模系统里,反馈是即时的,反馈会强化手段;在这个小规模环境里,动作和目标具有高度一致性的个体,胜出的概率越大。但随着系统规模变大,反馈滞后且混沌,没有快速见效的方式;过去一致性越强的样本,改变自身的阻力越大,倒下的概率越大。
这是成长的“一致性悖论”。
(我不知道是否可以解释为:规模是汪老师所说“参量域”中的重要参量。)
我想真正的高手不是小规模里最灵活的那一个,也不是大规模里最体系化的那个,而是能够阻断认知惯性——在小规模时储备大规模的能力,在大规模时随时做好降维回小规模的准备。
庄子说,无用之用,是为大用。
或许无用之用,不是无用,而是我们尚未长到需要它的规模。
汪丁丁:我很喜欢郑子拓的发言,不仅表扬,而且,喜欢,尤其是这篇发言的结语。郑子拓,文如其人,坐在前排,时而沉思,时而看我,还突然冒出那一惊人之语。对组织内的个体而言,组织的规模当然是个体感受域依赖的参量。
郑子拓:谢谢汪老师,您的内容引发了很多思考,颇有收获。
刘玉申:阻断认知惯性本应有其边界——参量域的调整需与时间进程、所处环境动态适配,终究要因时因地制宜、因人而异。若一个人已然安于现状,既对自我状态满意,又不影响他人,那么以平和愉悦的心态顺应自然、安然度过余生,何尝不是一种难得的幸福?作为一个智商一般的普通人 我是这么想的[害羞]
王珊珊:自然的选择本来就是在进化中的,那么如果能心情愉悦地跟上自然的变化,是不是也就意味着自己的参量域在被动且良性地提高和调整呢[呲牙]
刘玉申:[强][强]
李丹:就像大模型无法超越它所预训练的数据分布,人类也极罕见能摆脱自己的反馈闭环,尤其是那些曾经的正反馈闭环。更不要说大型组织。作为人类,祈求自己带有那种天赋,作为组织,需要换头。
冯静静:通过个体的内外参量域,找到对应的相对稳定的感受域,可以评估预测其重要性感受价值排序,就可以理解每个人的如其所是,没有比较和焦虑,社会如此和谐。可是现实多是错位,所以懂得变通如此重要和可贵。
汪丁丁2025年11月25日朋友圈Elusive Cur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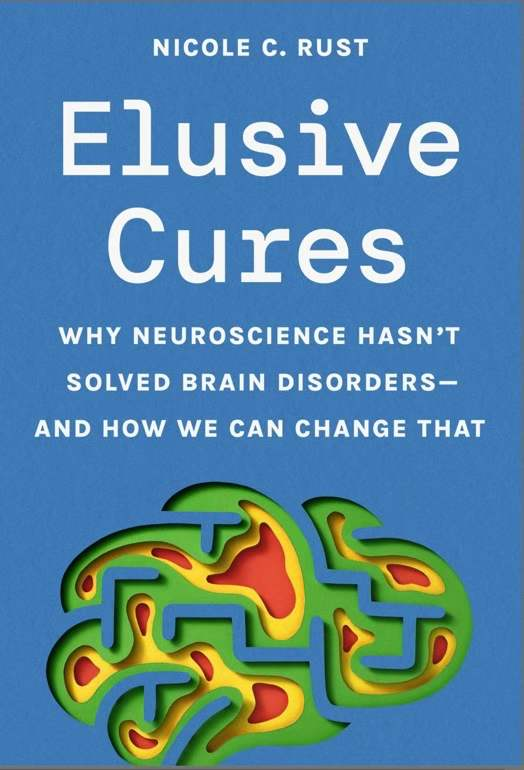
图1:Nicole C Rust 2025 Elusive Cures --- Why Neuroscience Hasn’t Solved Brain Disorders and How We Can Change That,
微信读书的译文:妮可·拉斯特,2025,难以捉摸的治愈方法:为什么神经科学没有解决脑部疾病——以及我们如何改变这一点。

作者是UPenn(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脑科学家和心理学教授,岁数不大,却已从事脑科学研究二十多年。
我是1998年开始研读脑科学的,至今也已二十多年。当然,她研究脑在分子水平上的活动,称为“分子神经科学”。我喜欢这本书,因为,在半个世纪的脑科学曲折进展之后,终于,我再次看到学术界出现了这样一本书,重新思考全部领域并建议她认为是“新的”研究思路。其实,在我的理解里,她建议的脑科学研究思路,就是霍兰德在2012年或更早建议的复杂适应系统(CAS)。脑之为“现象”,当然是复杂适应系统的经典案例。只不过,脑科学研究始终不能在这一思路上开展,因为,实在过于复杂,难以奏效。即便读她这本书,我仍怀疑,如何研究“非线性的脑”(这是她使用的语言)。这本书开篇讲述的故事,与我多次推荐的于涵2022年著作的中译本《偷走心智的贼》里描述的关于老年痴呆症研究的状况完全一致。从2022年到2025年,这一领域进展缓慢,可见一斑。我摘录“微信读书”的译文“引言”,摘录,但仍很长,需要“跟帖”:
利用卡罗尔的家族提供的遗传物质,哈代的研究小组开始进行寻找突变的繁重工作,这一过程耗时 4 年。结果发现,罪魁祸首是 APP 基因中一个 DNA 碱基对的突变——一个“C”变成了“T”。这一突变导致蛋白质淀粉样β-蛋白中一个氨基酸(异亮氨酸代替缬氨酸)发生置换。研究人员也在另一个患病家族中确认了相同的突变。许多人称赞这一发现是“突破”。《纽约时报》报道称,“导致阿尔茨海默病的基因突变被发现。”发现这一发现的初级研究员艾莉森·戈特记得当时的想法是,“有时在科学领域,你会逐渐积累数据。而这一发现就像,突然间,灵光一现。”哈代回忆这一发现时说,“我觉得我们破解了阿尔茨海默病。我觉得我们做了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事。”一名研究员推测说,“我敢打赌,如果你能阻止淀粉样蛋白的积累,就能阻止痴呆症。”掌握了这些知识,哈代和其他研究人员继续发展了“淀粉样蛋白假说”。他们已经知道,阿洛伊斯·阿尔茨海默最初发现的斑块是由淀粉样蛋白-β组成的。这种蛋白质的基因突变导致卡罗尔家族和其他人患阿尔茨海默病的事实表明,斑块可能是这种疾病的原因(而不是结果)。淀粉样蛋白假说的要点是,APP(和其他因素)的突变导致淀粉样蛋白斑块的积累,由于这些斑块是有毒的,它们会引发一系列事件,导致神经退化;反过来,这会导致认知能力下降。这个假说很快成为阿尔茨海默病研究的主要焦点。研究人员从这里出发,开始探索如何清除大脑中的淀粉样斑块。经过多次失败后,脑部研究人员成功研制出一种药物来清除淀粉样斑块,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于 2021 年批准了第一种清除淀粉样斑块的药物 aducanumab,并于 2023 年批准了第二种类似药物 lecanemab。这两种药物都是与淀粉样β蛋白结合的抗体,可以触发身体清除大脑中的斑块。它们都很好地完成了这项工作,这本身就是值得注意的。到目前为止,关于阿尔茨海默症的故事的一切都是如此令人难以置信,以至于要告诉你这个转折点,我感到心碎。
这些淀粉样蛋白清除剂有希望阻止阿尔茨海默症,但临床试验表明,它们只能适度减缓认知能力下降的速度。在这两种药物中,lecanemab的临床试验是最有希望的,它显示了适度的减缓作用,预计可将病程延长约9个月。不幸的是,这种药物也有副作用,比如增加脑肿胀的风险。它有帮助,这是关键的一步,但遗憾的是,它不是最终的解决方案。为什么清除淀粉样蛋白的方法没有取得更好的效果呢?目前尚不清楚。人们仍然希望这些药物能发挥很好的作用,但在疾病发展的早期阶段,这些药物并没有起到预防神经退化的作用。来自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突变(如卡罗尔家)的证据表明,阿尔茨海默氏症的生物标志物可能在认知症状出现15年多前就开始出现;然而,在临床试验中,这些药物是在疾病发展的较晚阶段施用的。临床试验正在进行中,以确定更早地施用这些药物是否会产生更好的效果,每个人都翘首以盼。与此同时,一些人怀疑,如上所述,淀粉样蛋白假说可能并不完全正确,或者是不完整的。哈代持这种观点:“虽然(淀粉样蛋白假说)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它包含了一些真理的成分......但它显然没有从几个方面捕捉到疾病过程的复杂性。”其他人则推测其他诱因,如神经元内另一种蛋白质的积累,即tau,以及病毒和环境毒素。目前,没有人确切地知道。有关阿尔茨海默病的未完待续的故事,是科学成就的非凡记录,但并非皆大欢喜的结局,至少现在还不是。在发现 APP 突变后的 30 年里,卡罗尔作为该疾病的患者倡导者,分享了她的家庭故事,并激励了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和寻找治疗方法的研究人员之间的联系。因为没有治愈方法,她拒绝进行基因测试以确定她是否是携带者。不幸的是,她在 2012 年被诊断出患有该疾病,我们没有办法帮助她。在经历了阿尔茨海默病的各个阶段后,她于 2024 年 3 月死于该疾病。
让我们暂停一下,反思一下这个时间表:自从卡罗尔写信和哈代的团队发现APP后,已经过去了30多年,我们仍然没有找到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或治愈阿尔茨海默氏症的方法,即使对于像卡罗尔这样的家庭,我们可以追溯到基因突变。正如卡罗尔忠实的丈夫斯图尔特所说,“我们现在为孩子们而战。”那么,是什么阻碍了阿尔茨海默症的治疗方法呢?不幸的是,对于其他许多脑部疾病,我们也可以问同样的问题,包括亨廷顿氏病、帕金森氏病、多发性硬化症、癫痫、抑郁症、精神分裂症等等。虽然我们有办法减轻这些疾病的一些症状,但是我们还无法治愈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全球范围内,这些疾病的患者数量是惊人的。对于850万罹患帕金森氏症的人来说,我们有治疗方法来帮助他们减轻症状,但是没有办法减缓与该疾病相关的神经退变。令人震惊的是,全球有9.7亿人患有抑郁症、焦虑症或精神分裂症等精神障碍,其中约三分之一(3.23亿人)的症状对现有治疗具有抗药性。12亿人患有慢性疼痛,虽然最极端的病例可以用阿片类药物治疗,但这些药物会导致认知损伤和成瘾。这只是几个例子。2010年,脑部疾病每年给欧盟造成8000亿欧元的损失,比荷兰的国内生产总值还多,比癌症、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的总和还多。对2016年美国的类似估计表明,成本为1.5万亿美元,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9%。人类可以做很多令人惊叹的事情。我们可以飞到月球;我们可以与许多类型的癌症作斗争,使它们进入缓解期。那么,是什么阻碍我们治愈脑功能障碍呢?或者,在没有治愈方法的情况下,是什么阻碍了更有效的治疗方法呢?我是一名神经科学家,从事脑研究已有二十余载。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深信自己拥有世上最好的工作:拿钱思考关于大脑如何运作的新问题并解答它们。我的研究灵感很大程度上源于我对大脑如何产生意识、进而产生自我这一问题的强烈好奇。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我把注意力放在了记忆上。
我调查了如下问题:当我们有过在某处见过某物的经历时,我们的大脑里发生了什么?我们的大脑是如何做到记住这么多东西的?我们的大脑又是如何筛选记忆和遗忘的?我的工作不仅仅是由好奇心驱动的;我相信,对记忆如何工作的基本理解将有助于未来治疗和治愈记忆功能障碍,包括与年龄相关的痴呆症,如阿尔茨海默氏症。事实上,我的研究计划的一部分侧重于将我们对记忆的了解转化为开发治疗记忆障碍的早期阶段。我们的研究只是被称为从实验室到临床的方法的一个例子,其中基础研究发现是开发新的临床治疗方法的第一步。从实验台到病床旁的叙述在脑研究领域根深蒂固,以至于它通常不会受到质疑,甚至不会被讨论。脑研究人员都有他们自己的类比,就像我在所有研究资助申请中陈述的那样:“这项提案的目标是了解大脑如何存储记忆。这些结果可以用来治疗与年龄有关的失忆症等记忆缺陷。”毕竟,要修复某样东西,首先要了解它,对吧?显然是这样。但我们是否学到了正确的东西?过去几年,我开始质疑从实验室到床边的更广泛叙述,涉及大脑研究。简单地说,当涉及到大脑紊乱时,大脑研究中发现的有序进展并没有导致大脑功能紊乱的新治疗和治愈的有序进展。换句话说,在实验室里有很多被感知到的成功,而在病床边却很少,至少到目前为止。有一些例外——非常重要的例外。但床边一直被挫折所主导,对阿尔茨海默症所遇到的挫折的各种变化。大约在2011年,一些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世界上最大的六家制药公司决定停止大脑药物研发工作。此前多年,这些公司花费巨资让药物通过临床试验,但都以失败告终。这些公司总共在研发新药上投入了数十亿美元,仅阿尔茨海默症药物就投入了180亿美元,但收效甚微。问题出在哪里?有报道称,这些公司集体得出结论:我们对大脑还知之甚少,尚无法针对其功能障碍研制出新的药物疗法;投资大脑药物研发根本不划算。换句话说,除非我们在实验室里取得更多进展,否则临床研究进展将十分有限。总的来说,自2011年以来,情况并没有多大改变。我们仍然不了解大多数脑部疾病的病因。对于阿尔茨海默病和亨廷顿病,我们仍然缺乏任何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对于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等疾病,现有的治疗方法对某些人有效,但对其他人无效。这并不是说什么都没有发生——它发生了!无论以何种方式衡量,大脑研究的实际进展都在爆炸式增长,甚至神经科学教科书的页数。。。。。。
2023 年,哈代和他的同事开始倡导一种不同的阿尔茨海默氏症方法,我们不再假设导致阿尔茨海默氏症的事件表现为多米诺骨牌连锁反应,而是开始接受该系统更多的复杂性。哈迪现在提倡把与阿尔茨海默症相关的大脑系统建模为非线性的动态系统;在这些系统中,通常整体(如认知功能和功能障碍)不容易从其部分(如蛋白质)的运作中预测出来。把这称为视角的转变并不为过:“对于非线性的系统,相关性不意味着因果关系,因果关系不意味着相关性,甚至当涉及多重互动、反馈和时滞时,因果关系的概念也难以定义。”的确,这些类型的系统远非直观的。它们可以被理解;它们只是需要不同的方法,包括数学模型。假设大脑在阿尔茨海默氏症中失灵的部分作为非线性动力系统运行(正如我们将讨论的那样,这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哈代是对的——通过这种系统的透镜来解决这个问题可能是治疗阿尔茨海默氏症的唯一途径。这只是当今前沿脑科学研究的一个例子,我们将在本书中讨论更多这样的例子。正如我们将看到的,研究人员开始转变他们对大脑的看法,从分子神经科学框架的骨牌式连锁思维,转向更好地捕捉其复杂性的方式。但是,在前进的道路上航行是极其棘手的。为了接受更多的复杂性,我们可以从许多方面转变对大脑的看法。关于大脑的哪些想法将对实现有影响力的进展——甚至治愈——脑功能紊乱至关重要?在本书中,我将带大家沿着一条精简的路径,重走我曾经走过的道路,以询问并回答我在本书导言中提出的困难问题。我们将在第 1 部分开始,探讨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从我们迄今为止开发的治疗方法的历史(甚至许多脑部研究人员都不知道)开始。为了探索理解大脑和修复大脑之间的关系,我们将追溯精神分裂症、抑郁症和极端瘫痪等疾病治疗方法背后的发现故事,找出导致这些科学突破的原因。作为剧透,除非你真的知道,否则它可能不会像你想象的那样奏效(bench to bedside 这个短语显然不能很好地描述这一点)。在第二部分中,我们将探讨大脑研究人员如何详细阐述分子神经科学框架,以解决其三大问题。第一个详细阐述试图通过将大脑视为一种“计算机”来填补大脑和思想之间的空白:一种接收感官输入并执行计算以确定其行为方式的信息处理机器。虽然这种方法为设计新药提供了很大希望(并促进了人工智能的有意义发展),但它只能让我们走完旅程的一半,因为它继续将大脑过度简单化,将其视为多米诺骨牌链。第二种解释认为,我们不应该把大脑看作是一连串的多米诺骨牌,而应该把它看作是一个需要反馈来调节其稳定性和灵活性的系统。它认为大脑是一个复杂的自适应系统,在处理信息的同时调节自身,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其适应性。我们将看到这种方法更加有前途。在第三部分中,我们将探讨这种对大脑复杂性的新发现如何改变大脑研究人员寻找大脑功能紊乱的原因以及如何治疗的方法。我将概述下一步的大脑研究,这些研究将需要解锁大脑最大的谜团,并带来新的治疗方法,帮助数十亿正在受苦的患者。在最后一章中,我将描述为什么我如此乐观地认为,未来几十年的大脑研究将比过去几十年更具影响力。这本书的灵感来源于我对大脑研究前景的日益悲观。在写作这本书的同时,我无疑是乐观的。这种新的风气将对我在“实验台”上进行研究的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我已准备好全心全意地接受这些变化。大脑研究正处于一个新时代的转折点。既然我能看到事情正在发生变化,我很高兴能与你们分享这一愿景。在我们深入探讨之前,先简单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写作水平。我坚信,清晰透彻的思考和几乎人人都能理解的直白解释,将使脑科学研究受益匪浅。虽然大脑很复杂,脑科学研究也很专业,但幸运的是,这些问题都是概念性的,而概念本身也相当直白。对于从事脑科学研究的专家来说,关于脑科学研究前景的想法非常重要,但不仅限于研究人员;对于任何受到某种脑功能障碍影响的人,或者任何有亲人受到影响的人来说,对于政策制定者、记者,以及任何想更好地了解大脑的人来说,这些想法都非常重要。了解大脑与我们所有人都息息相关。我们所有人都应该了解解决问题的办法,这很有道理。
课程:收益递增经济学,课程纪要由教务老师杨昕整理。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