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喜欢这幅插图,它来自2020年出版的《Artificial Psychology: Psychological Modeling and Testing of AI Systems》,标题应直译为,“人工智能心理学:人工智能系统的心理建模与检测”。这本小册子的导言,以这幅插图开篇,我在插图里写了我的直译。导言结束时,作者写了这样一段文字:毕竟,这样的人工智能系统不能令人满意,如果它这样回答那个令人困窘的问题:“No Dave, I don’t think I can do that”(不,大卫,我不认为我能为此感到害羞)。我想到2018年世界意识大会的前三位主题发言人的第二位,在以前的文章里,我提及第一位是著名的彭罗斯,他在演讲的后半部分报告他与合作者的宇宙学模型意味着“意识在物质之前存在”。第二位演讲人介绍他领导研制的“量子计算”项目,他的英语带有德国口音,在演讲的后半部分,他试图定义量子计算机的“情感”。例如,“快乐”,他说,当量子计算达到预期的效果时,它可能感到快乐。于是,我认为他可能继续想象,当量子计算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时,它感到痛苦。我在行为经济学课程的开篇通常要介绍人类通有的五种原初情感,“fear,sad,happiness,anger and disgusting”(惧、悲、喜、怒、厌),以及由这些原初情感复合而生的“次级情感”,依文化差异而有不同的语言表达,例如,“悲喜交集”。当然,还有更复杂的“三级情感”,例如,“五味杂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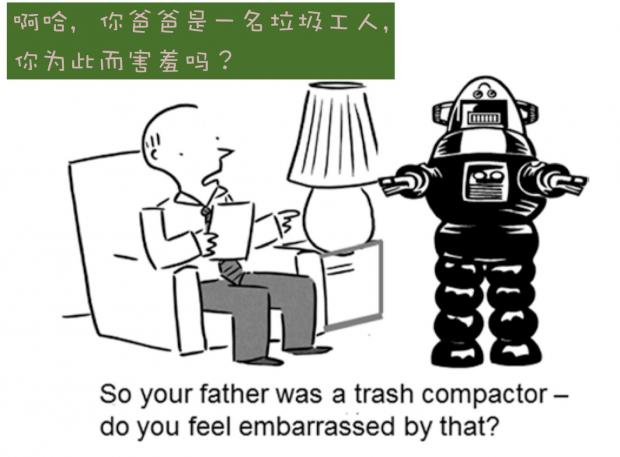
人类情感的脑科学研究表明,“embarrassment”这一情感的复杂程度可能要高于二级,也许还高于三级,以致,它在汉语里没有很好的对应单词。在这幅插图里,若以口语表达,我认为最合适的词是“丢脸”,若坚持以书面语表达,我选择“害羞”。这两种表达都不贴切,但在目前流行的汉语背景下,我不愿意使用“窘”这一单词。关于语言差异能够反映各族群之间的情感差异,我更喜欢使用的例子是,英语单词“Schaudenfrued”,原本不是英语,它来自德语,若译为英文就要用至少两个单词构成的短语,不如直接套用德语的原词。然而,这个词在汉语里早有对应,“幸灾乐祸”,它的英文注释是:以他人痛苦为自己快乐的源泉。德国的经济学家何梦笔,也是一位汉学家,他二十年前对我说他发现德语和汉语的思维结构远比其它语言更接近。
回到主题,这本小册子探讨的人工智能心理学,主题是“人机合作”时发生于人类这一方的“信任感”和发生于机器这一方的“可信度”。我能想象的一种可能是,人工智能机器人既然不能感受生物感受到的那些重要性,那么,它们将控制人类并由人类在广域竞争中为它们提供它们生存所需的能源。能控制人类的机器人,在这一意义上,于是成为“广域智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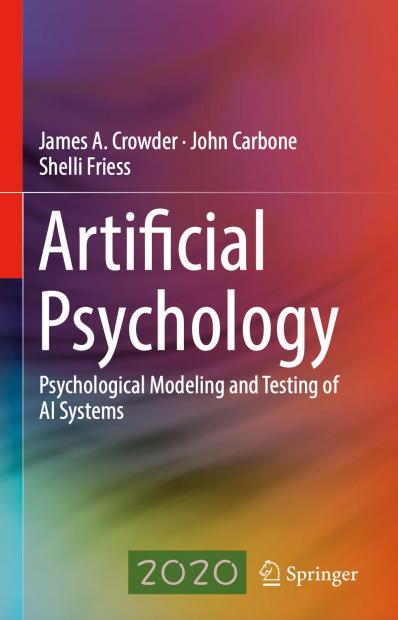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